下班后仍要手机不离手,频频回微信工作群消息,如何消除打工人“为群所困”“休而不息”的烦恼?继去年两会呼吁打破“35岁职场门槛”后,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再次聚焦职场人的痛点,呼吁保障劳动者离线休息权。
不久前,一则热搜引起吕国泉的关注。四川一名店铺设计师称,从业两年多累积了600多个工作群,每天“24小时待命”“为群所困”,不敢关手机,离职后花3个半小时退群……结合此前“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新闻,吕国泉表示,这些案例均折射出了许多劳动者对休息权的渴求与无奈。
![图片[1] - 下班了还得“在线”!他呼吁“离线权”入法 - 万事屋 | 生活·动漫·娱乐综合社区-银魂同好聚集地](https://www.rei3.com/wp-content/uploads/2024/03/8ca654d9fea745c495e72c4d5e9df6a4noop.image_.webp)
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受访者供图
他在提案中提到,一些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进工作群,下班时间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等方式安排工作,劳动者“休而不息”“人在曹营心在汉”,休息权、隐私权得不到保障。还有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24小时在线,有的劳动者下班后因未及时回复信息,或没有打卡、线上开会、点赞转发等遭到批评、罚款甚至被开除。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数字信息技术正在模糊工作与生活的“边界”,“隐形加班”日趋常态化。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2022》,84.7%职场人在下班后仍会关注工作相关信息,40.5%职场人加班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职场人为“群”所困,怎么破?吕国泉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在劳动法立法层面引入离线休息权——即在法定或约定工作时间之外,劳动者享有拒绝通过数字工具进行工作联络或处理工作事宜的权利。
事实上,离线休息权在国外的一些立法中已有体现。2016年法国在劳动法典中提出了离线休息权,即“断开工作网络连接从而不接受雇主指示和提供工作的权利”。欧盟2021年也发布了《关于欧盟委员会离线权建议的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层面提出有关劳动者“离线权”的立法,并对成员国的有关立法进行确认与指导。
在国内,虽然国家层面还未确立保护离线休息权的法律规定,但面对“下班后回复工作微信,算不算加班”的争议,已有相关司法实践。在一些个案中,法院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明确将下班后利用微信付出实质性劳动认定为加班。
南都记者注意到,近期北京高院发布的法院工作报告中披露了一起案例,原告李某是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产品运营,经常在下班后或假期使用微信、钉钉与客户沟通,为此主张公司应该支付加班费。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支持了李某的诉求,判定公司应支付3万元加班费。
现阶段在立法之外,还可以怎么保障劳动者的离线休息权?吕国泉建议修订标准工时,对线上加班和工时补偿作出明确界定。他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加大数字经济背景下工资、工时、休息、休假等方面劳动基准制度研究规范,将工时基准保障纳入劳动保障机制。厘定线上线下工作时间边界,针对依托网络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强度大的岗位作出工作时限的制度性安排。将当前以工资为重点的集体协商拓展为包括工时等劳动基准在内的综合性集体协商机制,综合考虑线上加班频率、时长、工资标准、工作内容等因素酌情认定加班费。指导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列入界定、补偿离线休息权的条款,约定线上加班补偿标准。
同时,吕国泉认为有必要强化执法保障。对用人单位隐形加班行为,执法部门要加大监管和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健全维权机制,让劳动者在面对不合理无偿加班时有维权渠道。纪检监察等部门监督政务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防止工作群组强制使用、过度留痕、滥用排名等“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现象,为基层干部和一线劳动者松绑减负。
吕国泉还建议,引导用人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督促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合理安排工作定额和休息时间,保持员工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南都评论
写入法律,“离线休息权”才能更好落地
下班后还要不要回复工作短信?类似的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能算问题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离线加班这种操作。数字信息时代的技术变革,不断模糊人们工作与生活的边界,隐性加班已经肆无忌惮。近日,也有政协委员呼吁为基层工作者“指尖减负”,以戒除各种形式主义的所谓“工作留痕”,其实也与“离线休息权”的提案形成呼应。
来自全国总工会的政协委员持续关注职场痛点,并为之寻找可行的制度化解决方案,可以说专业对口。而社交平台对该份提案的差异性态度又折射出普通职场打工人最现实的无力感:很多网友可能支持政协委员为“离线休息权”鼓与呼,但在真的遭遇需要主张离线休息权的现实场景时,不少人又会选择沉默。
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休息权,不管是否有数字信息技术的“掺和”,都毫无疑问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障。即便是没有在具体的法典中明确写入“离线休息权”的字眼,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保障劳动者在新业态工作场景中包括休息在内的基本权利,司法的态度其实是明确的。此前面对“下班后回复工作微信,算不算加班”的争议,相关司法实践的态度也广受好评,法院通过个案判决进一步阐明,下班后利用微信付出实质性劳动应认定为加班。
但同时也要看到,个案认定休息时间的线上工作应为加班,是从劳动行为确认的角度表明了司法态度,这与明确支持劳动者有权在休息时间选择以离线的方式保障自身休息权益,还是有一定区别。另一种颇为尴尬的情况是,无论对于“线上加班”事实的主张,还是对“休息时间拒绝在线”的实践,可能往往都意味着具体劳动关系在进入末端纠纷状态,而极少可能一边主张权利,一边同时维持劳动关系的稳定。
政协委员力主“离线休息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写入法律,本身是在细化现行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休息权内容,是立法作为一种价值宣示载体的应有之义。
立法明确“离线休息权”,与实践中劳动者可能轻易不会主张相关权利事实上并不冲突——既然“离线休息权”有希望成为一项明确的法律权利,就可以保留,也可以放弃,但法律对劳动者相关权益的保障态度却一直都在场,随时可以被主张。
事实上,在劳资纠纷出现时,劳动者据以维护自身权益的各种法律依据,在纠纷发生之前也大概率不会被打工人时不时挂在嘴上。当然,在常态化的劳资谈判、劳动监察执法中,法律有明文规定还是可以为之提供更充足的底气。这也给各种张不开嘴、说不出口的劳动者权益,提供了更多督促执法监管介入的路径。
劳动关系的达成,本身就是各方权利不断博弈的结果。这么说起来,即便一次提案不足以促成法律修改,但“离线休息权”的公共讨论依然多多益善。普通打工人的苦衷,应该在更多空间被提出、被讨论、被正视,才能为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创造条件。
来源:南方都市报
文是楼上发的,图是楼上帖的,寻仇请认准对象。
有些是原创,有些图文皆转载,如有侵权,请联系告知,必删。
如果不爽,请怼作者,吐槽君和你们是一伙的!请勿伤及无辜...
本站所有原创帖均可复制、搬运,开网站就是为了大家一起乐乐,不在乎版权。
对了,本站小水管,垃圾服务器,请不要采集,吐槽君纯属用爱发电,经不起折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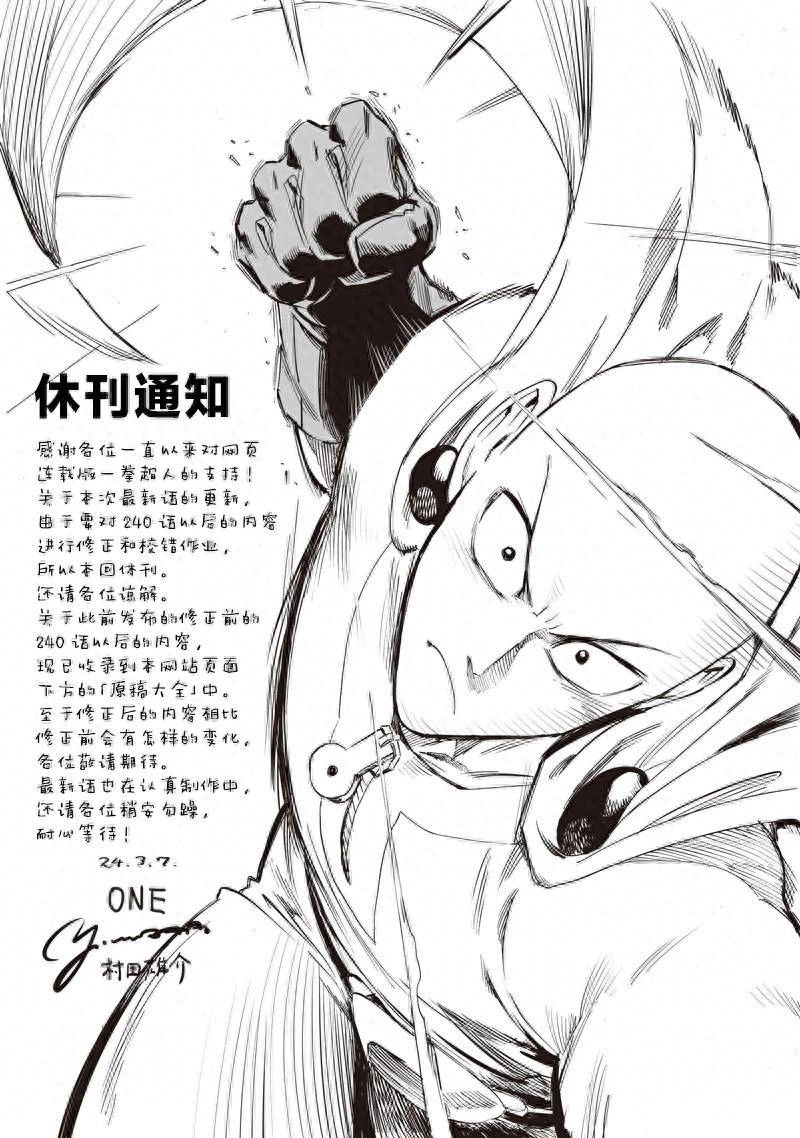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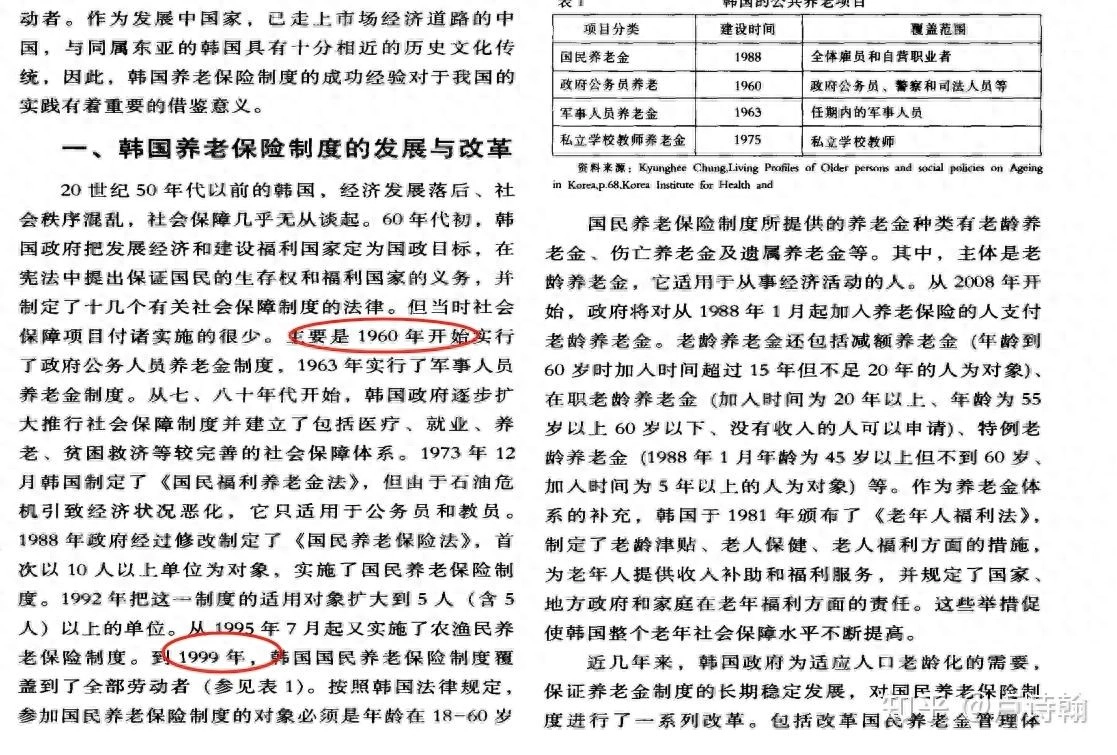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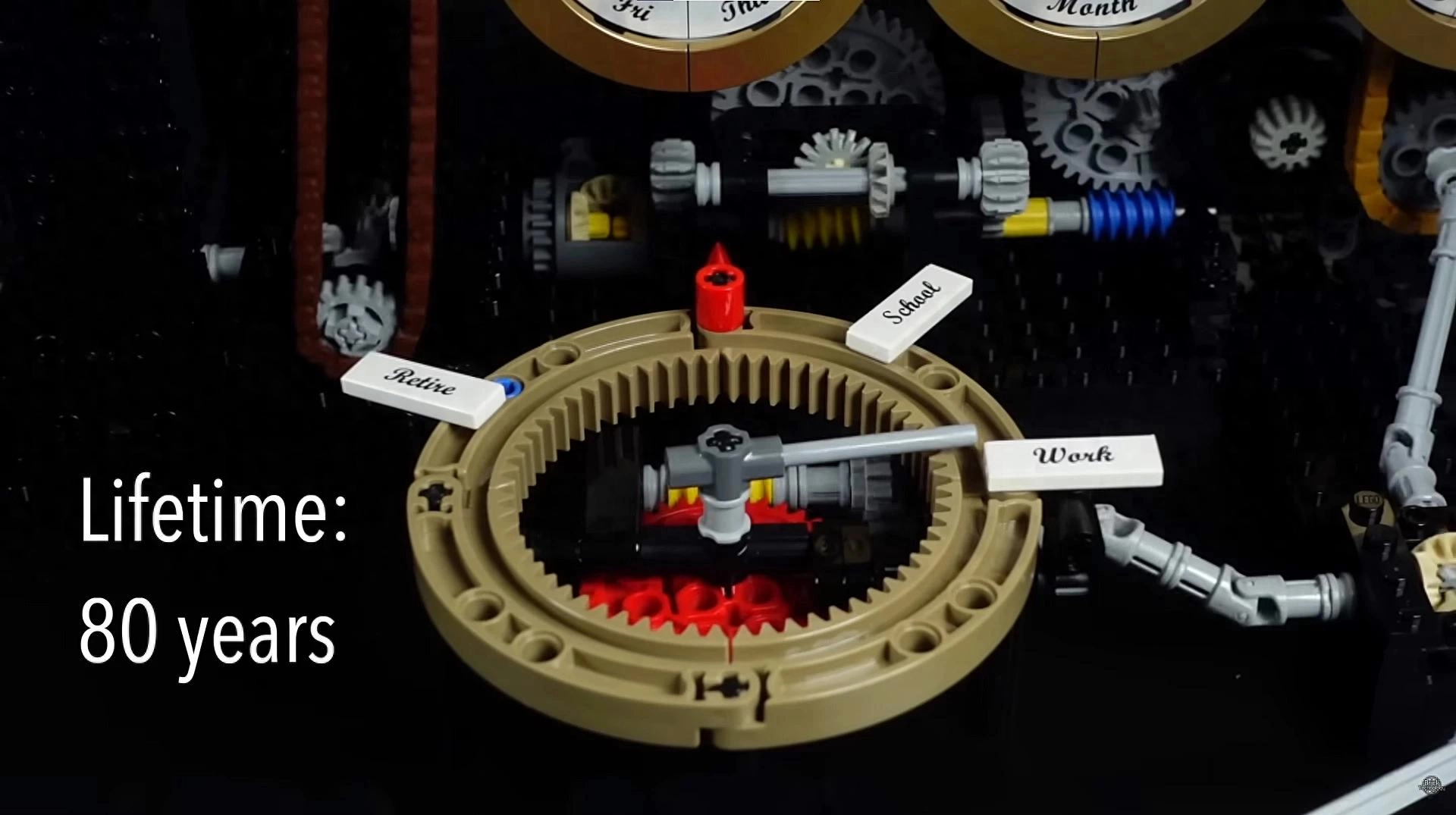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